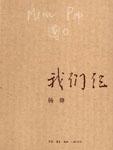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
(十四)
我们这间房,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,但没有横格。年轻人用干校带回的破木箱,为我们横七竖八地搭成格子,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木格子里。顶着西墙,横放两张行军床。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,权当床头柜兼衣柜。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,那是锺书工作用的。近南窗,贴着西墙,靠着床,是一张小书桌,我工作用的。我正在翻译,桌子只容一沓稿纸和一本书,许多种大词典都摊放床上。我除了这间屋子,没有别处可以容身,所以我也相当于挪不开的物件。近门有个洗脸架,旁有水桶和小水缸,权充上下水道。铁架子顶上搭一条木板,放锅碗瓢盆。暖气片供暖不足,屋子里还找出了空处,生上一只煤炉,旁边叠几块蜂窝煤。门口还挂着夏日挡蚊子冬日挡风的竹帘子。
十一月二十日,我译完《堂·吉诃德》上下集(共八册),全部定稿。锺书写的《管锥编》初稿亦已完毕。我们轻松愉快地同到女儿家,住了几天,又回到学部的陋室。因为在那间屋里,锺书查阅图书资料特方便。校订《管锥编》随时需要查书,可立即解决问题。
我们住的房间是危险房,因为原先曾用作储藏室,封闭的几年间,冬天生了暖气,积聚不散,把房子胀裂,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。不过墙外还抹着灰泥,并不漏风。我们知道房子是混凝土筑成,很坚固,顶上也不是预制板,只二层高,并不危险。
“斯是陋室”,但锺书翻译毛主席诗词的工作,是在这间屋里完成的。
这年的十月六九九藏书日“四人帮”被捕,报信者只敢写在手纸上,随手就把手纸撕毁。好振奋人心的消息!
我们在师大,有阿瑗的许多朋友照顾;搬入学部七楼,又有文学所、外文所的许多年轻人照顾。所以我们在这间陋室里,也可以安居乐业。锺书的“大舌头”最早恢复正常,渐渐手能写字,但两脚还不能走路。他继续写他的《管锥编》,我继续翻译《堂·吉诃德》。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,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,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。
办公室并不大,兼供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。西尽头的走廊是我们的厨房兼堆煤饼。邻室都和我们差不多,一室一家;走廊是家家的厨房。女厕在邻近,男厕在东尽头。锺书绝没有本领走过那条堆满杂物的长走廊。他只能“足不出户”。
“嘤其鸣兮,求其友声。”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,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。锺书是坐冷板凳的,他的学问也是冷门。他曾和我说:“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。”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己,不求有名有声。
锺书脚力渐渐恢复,工作之余,常和我同到日坛公园散步。我们仍称“探险”。因为我们在一起,随处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。我们还像年轻时那么兴致好,对什么都有兴趣。
叶君健不嫌简陋,每天欣然跑来,和锺书脚对脚坐在书桌对面。袁水拍只好坐在侧面,竟没处容膝。周珏良有时来代表乔冠华。他挤坐在锺书旁边的椅上。据说:“锺书同志不懂诗词,请赵朴初同志来指点指点。”赵
九九藏书网朴初和周珏良不是同时来,他们只来过两三次。幸好所有的人没一个胖子,满屋的窄道里都走得通。毛主席诗词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间陋室里完成的。一九七四年冬十一月,袁水拍同志来访说:“江青同志说的,‘五人小组’并未解散,锺书同志当把工作做完。”我至今不知“五人小组”是哪五人。我只知这项工作是一九六四年开始的。乔冠华同志常用他的汽车送锺书回家,也常到我们家来坐坐,说说闲话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工作停顿,我们和乔冠华同志完全失去联系。叶君健先生是成员之一。另二人不知是谁。这事我以为是由周总理领导的。但是我没有问过,只觉得江青“抓尖儿卖乖”,抢着来领导这项工作。我立即回答袁水拍说:“钱锺书病着呢。他歪歪倒倒地,只能在这屋里待着,不能出门。”
不过这间房间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。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就在我们前面的六号楼里。锺书曾是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委员会主任,选书、买书是他的特长。中文的善本、孤本书籍,能买到的他都买。外文(包括英、法、德、意等)的经典作品以及现当代的主流作品,应有尽有。外宾来参观,都惊诧文学所图书资料的精当完美。而管理图书资料的一位年轻人,又是锺书流亡师大时经常来关心和帮忙的。外文所相离不远。住在外文所的年轻人也都近在咫尺。
一九七五年的国庆日,锺书得到国宴的请帖,他请了病假。下午袁水拍来说:“江青同志特地为你们准
99lib.net备了一辆小轿车,接两位去游园。”锺书说:“我国宴都没能去。”袁说:“锺书同志不能去,杨绛同志可以去呀。”我说:“今天阿姨放假,我还得做晚饭,还得看着病人呢。”我对袁水拍同志实在很抱歉,我并不愿意得罪他,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们俩之间,只好对不起他了。毛主席的诗词翻译完毕,听说还开了庆功会,并飞往全国各地征求意见。反正钱锺书已不复是少不了的人;以后的事,我们只在事后听说而已。钱锺书的病随即完全好了。但是所内年轻人不放心。外文所的楼最不坚固,所以让居住楼里的人避居最安全的圆穹顶大食堂。外文所的年轻人就把我们两张行军床以及日用必需品都搬入大食堂,并为我们占了最安全的地方。我们阿姨不来做饭了,我们轮着吃年轻人家的饭,“一家家吃将来”。锺书始终未能回外文所工作,但外文所的年轻人都对他爱护备至。我一方面感激他们,一方面也为锺书骄傲。
袁水拍同志几次想改善工作环境,可是我和锺书很顽固。他先说,屋子太小了,得换个房子。我和锺书异口同声:一个说“这里很舒服”;一个说“这里很方便”。我们说明借书如何方便,如何有人照顾,等等,反正就是表示坚定不搬。袁辞去后,我和锺书咧着嘴做鬼脸说:“我们要江青给房子!”然后传来江青的话:“锺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,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,照顾锺书同志。”我不客气地说:“我不会照顾人,我还要阿姨照顾呢。”过99lib.net一天,江青又传话:“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。”我们两个没有心理准备,两人都呆着脸,一言不发。我不知道袁水拍是怎么回话的。
钱瑗在我们两人都下放干校期间,偶曾帮助过一位当时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,帮她解决了一些困难。老太太受过高等教育,精明能干,是一位著名总工程师的夫人。她感激阿瑗,和她结识后,就看中她做自己的儿媳妇,哄阿瑗到她家去。阿瑗哄不动。老太太就等我们由干校回京后,亲自登门找我。她让我和锺书见到了她的儿子;要求让她儿子和阿瑗交交朋友。我们都同意了。可是阿瑗对我说:“妈妈,我不结婚了,我陪着爸爸妈妈。”我们都不愿勉强她。我只说:“将来我们都是要走的,撇下你一个人,我们放得下心吗?”阿瑗是个孝顺女儿,我们也不忍多用这种话对她施加压力。可是老太太那方努力不懈,终于在一九七四年,我们搬入学部办公室的同一个月里,老太太把阿瑗娶到了她家。我们知道阿瑗有了一个美好的家,虽然身处陋室,心上也很安适。我的女婿还保留着锺书和老太太之间的信札,我附在此文末尾的附录二。
我们的女儿女婿都来看顾我们。他们作了更安全的措施,接我们到他们家去住。所内年轻朋友因满街都住着避震的人,一路护着我们到女儿家去。我回忆起地震的时期,心上特别温馨。
这年冬天,锺书和我差点儿给煤气熏死。我们没注意到烟囱管出口堵塞。我临睡服安眠药,睡中闻到煤气味,却怎么也醒不www.99lib•net过来;正挣扎着要醒,忽听得锺书整个人摔倒在地的声音。这沉重的一声,帮我醒了过来。我迅速穿衣起床,三脚两步过去给倒地的锺书裹上厚棉衣,立即打开北窗。他也是睡中闻到煤气,急起开窗,但头晕倒下,脑门子磕在暖气片上,又跌下地。我把他扶上床,又开了南窗。然后给他戴上帽子,围上围巾,严严地包裹好;自己也像严冬在露天过夜那样穿戴着。我们挤坐一处等天亮。南北门窗洞开,屋子小,一会儿煤气就散尽了。锺书居然没有着凉感冒哮喘。亏得他沉重地摔那一跤,帮我醒了过来。不然的话,我们两个就双双中毒死了。他脑门子上留下小小一道伤痕,几年后才消失。
对方表示:钱锺书不能出门,小组可以到这屋里来工作。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
一九七六年,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。这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地震,余震不绝,使我们觉得伟人去世,震荡大地,老百姓都在风雨飘摇之中。
《管锥编》是干校回来后动笔的,在这间办公室内完成初稿,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的产物。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,不用浅易的文言,而用艰深的文言。当时,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,正逞威横行。《管锥编》这类著作,他们容许吗?锺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,他不用炫耀学问。